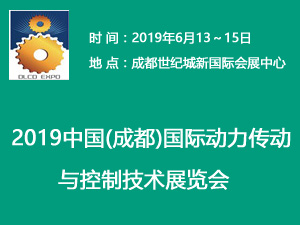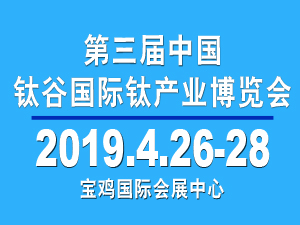燃料電池汽車正在悄然崛起。
早在1992年,日本豐田汽車就開始研究氫燃料電池汽車,當時起名為FCHV。經過10多年的技術積累,在2014年底,豐田Mirai正式面世發售。
隨著技術的突破,燃料電池汽車的發展速度越來越快。相關數據顯示,2013~2017年,全球氫燃料電池汽車銷量僅為6475輛,其中,大部分為豐田的Mirai系列;2018年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,合計銷售5525輛;2019年全球銷量增至7500輛。
燃料電池車在國內的發展軌跡也逐漸清晰。
2018年,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考察日本豐田汽車北海道廠區,參觀了Mirai燃料電池轎車。
國家層面對燃料電池車的重視程度可見一斑。然而,有一款關鍵材料一直制約著國內燃料電池車的發展。
燃料電池是燃料電池汽車的核心部件之一,燃料電池的關鍵材料之一則是催化劑,而催化劑的作用是使氧氣與儲氫罐中的氫氣發生電化學反應,為車提供驅動能量。
但早前,國內的催化劑主要依賴進口,交貨周期長、成本高,給國內燃料電池產業鏈發展帶來局限。
2019年,國內一家企業宣布其催化劑產品實現量產,為國內燃料電池車的發展帶來更多可能。這家企業就是上海濟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(以下簡稱“上海濟平”)。
破解進口依賴困境
國家相關政府部門已多次釋放出“加快推進氫燃料電池汽車產業發展”的信號。
中國科學院院士歐陽明高預計,到2020年,中國市場將會有5000輛到10000輛氫燃料電池汽車;2025年,市場的規模或將達到5萬~10萬輛。
“鋰電池車和燃料電池車是互補的。城際城市之間的代步,鋰電車是最好的,而遠途城市之間的交通使用燃料電池車更理想。因為加氫速度快一點,安全性能較高一些。”上海濟平副總裁劉瑾慧表示。
氫燃料電池汽車的市場增長無疑也將帶動催化劑的需求增長。業內專家介紹道,一輛普通家用小車大約需要80克催化劑,一輛營運客車大車則需要上百克。
車均用量不大,但其成本占比卻較高。
燃料電池的電堆包括膜電極、雙極板等組件,而催化劑是膜電極MEA的關鍵組成材料。在整個燃料電池中,催化劑成本占比最高。據賽瑞研究推算,在年產1000套燃料電池時,催化劑占總成本的26%,當年產電池數量達到10萬套或50萬套時,催化劑成本會達到40%左右。
“國內燃料電池催化劑80%到90%的原材料依賴進口,造成了極高的成本,而且供貨期不定。”劉瑾慧感慨道。
國內催化劑供應商主要有日本田中貴金屬、英國Johnson Matthey、比利時優美科等巨頭。
2018年,上海濟平成立。
“我們想幫助下游的產業來解決依賴進口這個重要問題,助力燃料電池產業在中國發展。”劉瑾慧說。
成立第二年,上海濟平便實現投產,并一舉拿下國產化催化劑市場的產銷第一,在國產化催化劑市場份額占比80%。
“我們有在燃料電池催化劑領域深耕20多年的專業人才,能快速地找到合適的設備、合適的碳載體,然后快速地進行量產。”劉瑾慧表示。
量產難度大門檻高
燃料電池催化劑量產難度有多大?
上海濟平之所以能快速拿下國產化催化劑市場80%份額,就有賴于其量產技術。
實際上,國內對于燃料電池催化劑的研究并不少,國產催化劑企業也有中科科創、喜瑪拉雅、擎動科技等。但中國工程院院士衣寶廉曾公開表示,國內研究催化劑的單位和企業,還拿不出催化劑裝車的運行數據。
換言之,下游客戶還沒有認可,商業化數據積累不夠充分。而客戶的認證,有多道門檻:耐久、成本低、一致性高等。
由于鉑金能使氫和氧高效反應,且反應穩定,可適應燃料電池內部復雜的化學環境和高電流密度,因此燃料電池催化劑多采用鉑金。
但鉑金催化劑容易“中毒”。遇到一氧化碳、氮氧化物或硫化物后無法“變出”質子,并且堆積在電堆里,反而影響電堆的壽命。
據業內人士介紹,國內實驗室的鉑金催化劑“中毒”等問題的解決尚不完美,仍未達到量產方面的要求,因此產業鏈更傾向于采用技術較為成熟的進口催化劑產品。
此外,對于催化劑企業而言,實現更大規模的量產需要具備相應的經驗和數據,而經驗和數據需要靠重金“砸”出來。
鉑屬于重要的貴金屬,其主要開采地南非每年僅開采100噸左右,價格難免昂貴。
劉瑾慧表示,每進行一次放大生產就意味著高昂的投入。從100克到200克、300克,每個環節的放大都關系到設備的調整,此外,制備環境、溶液都會隨之發生變化。
但凡經歷一次失敗,對于企業而言沉沒成本動輒達到幾十萬元甚至上百萬元,“這需要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投入,所以真正能夠拿出量產產品的企業很少。”
“國外在催化劑這一塊的研制已經有數十年的歷史,他們有豐富的產業化經驗。”劉瑾慧表示,這是國內企業難以企及的水平。
在2019年的投產儀式上,上海濟平宣布一期催化劑年產量可達1500千克。
“國內很多企業日產量僅為100克到200克之間,很多時候是分批供貨。但是對客戶而言,一次性采購1千克和分5個批次采購200克相比,前者的成本、時間、一致性等無疑更具優勢。”劉瑾慧說。
2020年7月,上海濟平和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人民政府正式簽約設廠,項目投產后,預計可年產2噸催化劑,可配套2萬臺套電堆。
占領了技術制高點,上海濟平棋局進一步做大。
新生企業的市場棋局
盡快實現燃料電池催化劑進口替代,下游的呼聲無疑是高漲的,畢竟他們遭受店大欺客的現象,在過度依賴進口產品時時有發生。
劉瑾慧回憶道,曾有客戶購買進口的催化劑,最后檢查出氯含量超標,對催化劑性能產生嚴重影響。“一下就是幾百萬元砸在手上,而進口商卻推諉責任。”
據了解,形成本土化供應后,供貨期相較進口有所縮短,并且將形成比較穩定的供貨關系。
但面對這個剛成立2年的本土企業,對于其產品的可靠性,下游客戶難免犯嘀咕。
“客戶的信任是有一個過程的。”成立初,劉瑾慧帶著產品去找客戶,結果碰了一鼻子灰,客戶明確表示不考慮國產催化劑,并且對這個新成立企業的技術存疑。“我聽到最多的一句話就是我目前不使用國產催化劑,有了大廠背書我們再用也不遲。”
對此,上海濟平的策略是抓住下游龍頭進行推廣,通過龍頭企業的背書,進一步向其他潛在客戶推廣。“效果十分明顯,被進口產品折磨過的客戶想先嘗試測試,然后從少量的試用開始。”
作為本土企業,上海濟平也為客戶增加了貼心的增值服務。如有新入行的客戶想做膜電極,但不清楚催化劑的漿液調配,上海濟平則通過分享催化劑的漿液調配等相關經驗,幫助他們把膜電極的性能做高。
上海濟平也在思考如何進一步降低催化劑成本。
其一便是根據客戶工藝和需求降低鉑載量。上海濟平的鉑合金催化劑產品的活性是鉑碳催化劑的兩倍,意味著使用0.2mg/cm2的鉑合金催化劑產品與0.4mg/cm2的常規的鉑碳效果是同等的。
其二是與上游的貴金屬材料商合作,將鉑價格鎖定在一定范圍內。
另外,尋找新的方向,如研發第二代催化劑——三元鉑合金催化劑,以求增進耐久性。“如果能夠量產的話,它大概可以降到鉑碳催化劑價格的60%。”
2019年鋰電新能源車的銷量突破百萬輛級,而燃料電池車銷量僅數千輛。
但劉瑾慧依然樂觀,“技術問題解決了,市場也會發展起來的,政策也會隨之而來,這樣又會帶動市場進一步發展。”